楊双子vs.瀟湘神/我們所有人都正在重新學飛

以娛樂的手段,
寫嚴肅的命題
●楊双子
瀟湘上回提到:「也聽過這世代的台灣書寫不過是政府刻意培植的說法,但身為大眾小說家,我只能表示遺憾。」你狀似輕描淡寫,實際我有同樣深刻的無奈。
如你所知,我也擔綱漫畫原作,漫畫《綺譚花物語》去年(2021年)秋天獲頒金漫獎年度漫畫獎,請恕我在此節錄當時上台發表的得獎感言:
自從1949年戒嚴以來,「台灣」這個詞彙乃至於它的實體,都成為了明確的禁忌。很長一段時間,台灣漫畫是不存在「現實世界的台灣」的。
近來出現許多結合台灣在地議題的漫畫,反而被某些讀者嘲諷,認為這是刻意將台灣特色、「台灣價值」作為賣點,強迫眾人埋單。其實所有「正常國家」所生產的作品,本來就會自然存在它的在地特色,也會自然地與當代議題進行對話,是過去的台灣創作受到扭曲而畸形,導致「台灣的現實世界」被避談了半個世紀,近年重新獲得正視而且得到該有的鎂光燈,我認為這並不能粗暴地視為行銷操作。有句話是這麼說的,「籠子裡出生的鳥,以為飛翔是一種病。」當代的台灣漫畫,我們所有人都正在重新學飛。
同年春天,社群網站因故出現一波台灣漫畫爭議,當中一派論者對於運用歷史元素與在地議題的台灣漫畫抱持反感,並且認定是此類生硬漫畫打壞台灣漫畫讀者的胃口、偏又占據台灣漫畫已經稀缺的官方資源。我這番得獎感言,正是對這派論者的有心回應。草擬這段發言時,我料想可能再次成為爭議的燃料,果然之後在網路上也有些聲音——我卻不吐不快。
豈止台灣漫畫創作者,當代台灣文學創作者也面臨同樣的質疑,僅僅是台灣文學的腳步走得比台灣漫畫快一些,也更早爭議過一輪(該說是N輪)罷了。畢竟時至今日,我書寫裡的台灣歷史元素,會被視為討好握有補助資源的民進黨政府,而著墨描繪日本時代裡的資產階級生活樣貌,則使我被視為皇民。(荒謬之處太多,總之省略吐槽。)我不能代言別人,但我相信同世代寫作者裡也不乏有雷同遭遇之人。
我想書寫自己關切的在地議題,重構這塊土地上發生過的故往之事,期間歷經漫長十數年時光的探索思辨與研究考據,無論創作與論述都有一貫的內在脈絡,統合成我個人的文學創作準則:「以娛樂的手段,寫嚴肅的命題。」即使我自認是類型文學寫作者,走的是日本分類「娛樂文學」那一條路線,努力面對在地讀者與在地市場,可是2022年的今天,終究我(們)仍必須面對目標讀者會提問「為何要創作台灣的故事」的事實。
我不願以無奈作結。說到目標讀者,我曾以為我很清楚知道我透過小說想要對話的對象,但這幾年越來越不敢確定,因為從我獲得的反饋來看,似乎我預設的目標讀者跟實際的讀者相當不同;原先的目標讀者是百合(Yuri)迷群,結果發現比例更多的是嚴肅文學讀者。看來「以娛樂的手段,寫嚴肅的命題」這一寫作路線,還存在著巨大的進步空間。接下來十年,我得埋頭苦幹才行。
話說瀟湘,也能談談你預設的目標讀者嗎?
●瀟湘神
聽聞双子被稱為皇民,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。要是認真觀看双子作品,自然知道双子批判殖民體制,或是說,批評以族群為框架而建構的不平等,以及不平等生出的輕慢心;只能說,某些自詡為「讀者」的人,或許不見得真的下過讀者工夫吧?
回到目標讀者的問題,其實我很少想這件事。倒不是自信,而是讀者太難捉摸了,看嚴肅文學的人,真的不會看輕小說、看動漫嗎?或許不少人是雜食的。雖然我寫通俗文學,但我很少基於「讀者想看這個」之類的理由寫作,畢竟所謂讀者可能是我的幻想啊!追逐那些虛幻的意見,或許反而會撲了個空呢。雖然不便代言,但双子也不會盲目追逐讀者意見吧?總之,比起想像的讀者,我更傾向追問身為讀者的自己:我想看怎樣的作品?換言之,我就是自己「目標讀者」的範本。
研究所時代,我跟友人說過想以通俗文學寫嚴肅的社會議題,這與双子說的「以娛樂的手段,寫嚴肅的命題」類似,但我是受到社會派推理小說影響。其實所謂的嚴肅議題,絕大部分都是舉目所及之事,只是大家習慣、麻木到當成不存在。對這樣的視若無睹,通俗文學卻能依託獵奇的表象——譬如謀殺——將無感的日常陌生化,使人重新產生「啊!這麼說來確實……」的意識。我喜歡這種浪漫,也想成為寫出這種作品的人。
或許有人會抱著疑慮吧,通俗文學真能處理嚴肅議題嗎?畢竟通俗文學總被放在嚴肅文學的對立面,彷彿嚴肅議題是專屬於嚴肅文學的……坦白說,邊界都是人幻想出來的,文學難道該被此束縛嗎?而且通俗文學當然能處理嚴肅議題,只是不同類型的通俗文學——科幻、奇幻、推理、言情——它們就像有不同專精的體育好手,雖非全能,但只要在自己的體育項目上就能好好發揮;我能斷言,在類型小說的主場上,它處理嚴肅議題的潛力甚至比嚴肅小說更精緻。
這並不奇怪。所謂的類型文學,就是作者與讀者培養共識,建構出群體——如推理迷——的文化想像。在這個過程中,當然有大量的類型複製,但複製的結果並非媚俗,而是透過內容的飽和刺激突變,進而以大量作品群擴張形式。最深知類型弱點並自我質疑的不是別人,正是類型的作者與讀者啊!所以當推理小說的黃金年代過去,我們終於開始懷疑:只要滿足知性趣味就夠了嗎?推理形式真的能保證真相嗎?推理能保證正義嗎?偵探是必要的嗎?這些自我質疑辯證了推理小說的形式與倫理學,並以此回應時代。我會說類型文學能更精緻地探究議題,就是因為類型內部的自我否定與辯證,遠遠超過外界想像;它們不需從零開始建構理論。
據我所知双子也有這種經驗。《花開時節》裡,主角穿越到過去的台中,正是對台灣言情小說最盛行的時代,大家並非穿越到過去的台灣,而是中國的回應。既然都要穿越,為何要前往遙遠的他方,而非腳下土地?這是重要的疑問,但要是言情小說沒有蓬勃發展,就不容易產生相關的意識。因此,通俗文學不處理嚴肅議題的印象,與其說是通俗文學的本質,不如說只是通俗文學的發展還不夠成熟。
且提個閒話。我聽過一種說法:寫得好的類型文學也算是文學。這話雖言之成理,卻不得我心;寫得好就是文學,這沒有疑義。但先將類型文學當成不入流的東西排除出去,再收割其優秀之作,是誰賦予文學這樣的立場呢?要誕生好的類型文本,仰賴的是類型的土壤,是作者與讀者短兵相接、主動回應包含社會風氣在內的議題最前線。將開得最美的花摘下,卻否認根柢的土壤?要是放任文學這樣做,那朵花也只能拿去當標本了——光閱讀「經典名著」是無法寫出好的類型文學的。
或許,嚴肅議題被嚴肅文學獨占的時代早已過去(甚至真的有這樣的時代嗎),双子說與你對話的更多是嚴肅文學而非通俗讀者,但是否能這麼說——這也可能是台灣通俗文學開始成熟的徵兆?當然,通俗文學沒有承擔嚴肅議題的義務,一切都是作者的選擇。但要說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就是判然二分、壁壘分明,那會不會只是一種畫地自限呢?雖是過分天真樂觀的觀察,但也不能說言不成理吧?也想知道双子的意見。

嚴肅文學與
通俗文學的邊界
●楊双子
「我能斷言,在類型小說的主場上,它處理嚴肅議題的潛力甚至比嚴肅小說更精緻。」瀟湘這番話,我無比贊同。你對「寫得好的類型文學也算是文學」這句話的不予苟同,我也深以為然。
瀟湘稱呼為「通俗文學」的,我慣稱為「大眾文學」,核心本質應該相同,請容我使用習慣的詞彙繼續這個話題吧。關於「嚴肅文學」與「大眾文學」的分野,討論起來至少需要足足兩個小時,姑且扼要地說,身為一名前‧大眾文學研究者,我認為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沒有真正「本質」上的差異,比如《紅樓夢》、《傲慢與偏見》等無數文學經典,在他們誕生之初是毫無疑問具備娛樂性質的大眾文學;相對來說,比如瓊瑤寫作一直以「文藝小說」自居並且早年獲得嚴肅文學場域(正所謂「文壇」)接納,卻在廣受消費市場歡迎以後遭「貶」為大眾文學。如果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存在「邊界」,要找到那個邊界,恐怕需要費幾部博士論文的功夫才行。
然而,我也必須申明這番論點是偏向學術觀點的,在現實世界裡,或許有部分讀者(尤其是類型讀者)會想:「我想看的書就是○○出版社和XX出版社出版的書」、「我都只看租書店裡面某某系列的小說」,從而認為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存在明確的分野也不一定。這種素樸的情感,真是羨慕啊……但即使是我十二、三歲開始泡租書店開始的那頭十年,我也是滿心困惑圖書館(嚴肅文學)和租書店(大眾文學)架上乍看毫無交流的作品,二者差異何在?而我想當的「作家」,又是哪一種「作家」?
說實話,這個話題再講一個鐘頭也沒問題,補充了還想補充,趕緊言歸正傳吧。瀟湘問我對二者邊界的意見,想必來自我前篇言及讀者組成:「原先的目標讀者是百合(Yuri)迷群,結果發現比例更多的是嚴肅文學讀者。」——這段話,實屬我為了省略說明而導致的語病,實在不好意思——精確的說,我指涉的是百合迷群與台灣文學學術圈兩種文化群體,而給予我回饋的更多來自後者。(當然,同時身處百合迷群與台灣文學學術圈兩種文化群體裡的讀者,就我個人感知上也是存在的。)
但是「目標讀者」的設定,意味著我要服務某一群我想像中的讀者嗎?那也還要分面向上來說,「目標讀者」作為商業用語,不免容易讓人有此聯想,不過我設想的更是「透過作品想要跟哪些人對話」,說穿了不免羞赧,這樣說來我並不是考慮「讀者想看這個」而寫,而是因為「我想讓讀者看這個」而寫吧。
另一方面,瀟湘說你考慮的是自己想看怎樣的作品,你就是自己「目標讀者」的範本。我也從這個角度想了一下我的寫作原點,人生前三十年,我寫作的第一個讀者永恆是双子姊妹中的妹妹若暉,比起我自己一個人想看的,我更考慮兩個人都想看的是怎樣的作品。那麼我目標讀者的範本,果然也是「楊双子」無誤。
這段日子跟瀟湘筆談,雖說沒有喝酒餐敘的場合暢快,卻別有一番激盪。未盡的談話,就留給下次見面吧!
●瀟湘神
我很期待。正好最近找到有趣的酒吧,延伸的問題就在酒吧裡好好聊吧。老實說,這段期間我常感到可惜,疫情改變了很多事,沒辦法像過去那樣頻繁聚會,許多話都卡在胸中,沒機會發展。這次筆談下來,或許是嚴肅,但暢談這些,彷彿回到疫情前的時光,對我來說實在是件快事。
其實過了一晚,我也覺得前面說得過了。就像双子所說,不受學術定義束縛的類型讀者,到書店裡根據書店分類探索自己有興趣的書籍,我們哪有立場予以否定呢?人們在認識上做出了區隔,肯定有現實生活中的需求。傲慢地將那些視為幻想,只是曝露了我個人的不成熟吧。
趁自省之際,再檢討一件事吧。對我們這樣的作者,書寫台灣題材是自然而然、未加造作之事;其實不只我們,在戰後初期……不,早從戰前開始,台灣的作者們就在書寫台灣的故事了,只是直到這幾年,台灣才走到鎂光燈下,被大家「發現」,如夢初醒。雖然我對「都是政府操控」之類的說法不以為然,放眼全世界,書寫土地都是再自然不過的,但我也不是完全無法理解為何會抗拒這樣的自然——
或許就像電影《媽的多重宇宙》裡說的,老歌不再好聽,世界不再熠熠生輝,這世界越來越糟了,但錯的是宇宙,不是自己。要是自己熟悉的敘事不再是世界運作的規則,或許我也會害怕不知所措吧?那時我也可能抓緊舊世界的殘骸,拿膠帶把它們拼揍起來,說服自己世界依然是那個世界,什麼都沒改變。
但事實是,這個時代沒有任何造作。沒有陰謀,也沒有迫害。如果文學需要真誠,那我們就只能接受「這個時代就是如此」;就算我對不喜歡台灣題材的言論不以為然,但也不必大放厥詞,說什麼看著吧,這就是台灣意識覺醒的時代之類的,因為一切都是真誠的結果,不過是那樣罷了。
無法適應這樣的時代,我想也是真誠的。但我希望能相信彼此的真誠。文學該是怎樣的、應該怎麼寫、該用怎樣的題材,要是只求建立不可動搖的權威,說那也太無聊了。倘若有一天我們能擺脫這種權力遊戲的延伸,或許文學就能迎來不同樣貌吧?在台灣文學的新時代,掃除權威的真誠能帶來怎樣的變化呢?我很期待。
八月《文學相對論》馬翊航vs.陳柏煜 將於8月1-2日登場 敬請期待!
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,精選好文不漏接!逛書店
猜你喜歡
贊助廣告
商品推薦
udn討論區
-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,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,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。
-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,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,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、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。不同意上述規範者,請勿張貼文章。
- 對於無意義、與本文無關、明知不實、謾罵之標籤,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、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。不同意上述規範者,請勿下標籤。
- 凡「暱稱」涉及謾罵、髒話穢言、侵害他人權利,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、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。不同意上述規範者,請勿張貼文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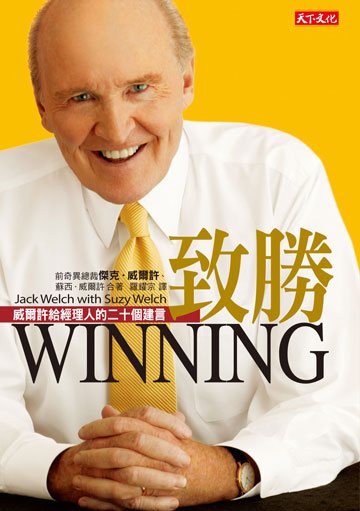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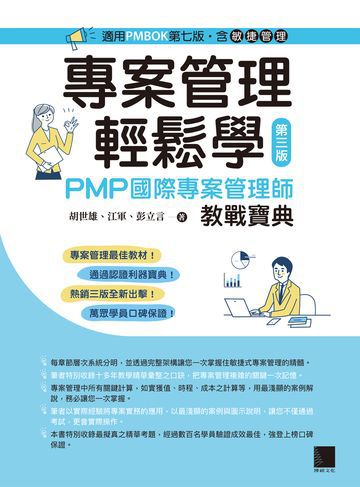





FB留言